刑事辩护
犯罪未遂的法律特性
发布时间:2020-04-15 浏览次数:1991
犯罪未遂的法律特性,是指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既遂相比所具有的特点。如果将犯罪预备形象地比喻为未能爆发的风暴,犯罪未遂则是一场已经爆发,但意外地未能造成应有损害的风暴。研究犯罪未遂的法律特性,有助于从实质上把握犯罪未遂的成立要件。
一、具有犯罪既遂的危险
犯罪未遂的一大特色在于法益已经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具有被毁灭的危险。犯罪预备行为对法益的威胁虽然是客观的,但却是潜在的,即法益尚未直接面临紧迫的危险。犯罪未遂行为则不同,其如同已经爆发的风暴,已经开始肆虐大地,法益已经直接面临着紧迫的危险,如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法益将会被毁灭。至于何种情形下行为具有犯罪既遂的可能性属于未遂行为,何种情形下不具有这种可能性属于预备行为,立法者撇开具体案件本身,使用“着手”一词对此加以区分。
既然创设侵犯法益危险的预备行为都是可罚的,那么,危险比犯罪预备行为更大的犯罪未遂行为更是可罚的。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看,未遂行为具有严重侵犯法益的客观危险性,是其处罚根据之所在。确认犯罪未遂行为侵犯法益的程度重于犯罪预备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可以合理确定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因为犯罪未遂侵犯法益的程度重于犯罪预备,所以,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要重于犯罪预备。若从主观主义的立场来解释为何对犯罪未遂的处罚重于犯罪预备,则比较困难,因为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在行为人意图侵犯法益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既然犯罪危险性没有区别,那么,对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处罚也不应当有所差别。不过,即使采取主观主义立场的学者,也都认为对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处罚应当有所区别。
另一方面,可以合理划定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可罚性范围:凡是某罪的犯罪预备具有可罚性,那么,该罪的犯罪未遂也具有可罚性。不仅如此,虽然某罪的犯罪预备不具有可罚性,但是该罪的犯罪未遂也有可能是可罚的,因为犯罪未遂在侵犯法益的程度上重于犯罪预备,预备行为本身对法益的侵犯性可能达不到可罚性的程度,但未遂行为对法益的侵犯性则有可能达到可罚性程度。所以,犯罪预备的可罚性范围小于犯罪未遂的可罚性范围是有其道理的。
二、非本人消灭既遂危险
犯罪未遂的另一特色在于虽然其具有犯罪既遂的危险,但事实上未能犯罪既遂。在已经着手实行但未能既遂这一点上,犯罪未遂与已经着手后的犯罪中止是相同的。那么,何以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重于犯罪中止?对此,主观主义的立场似乎找到了可以有所作为的天地,即犯罪未遂的行为人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导致未能犯罪既遂,而犯罪中止的行为人是基于己意自动防止了既遂结果的发生,可见犯罪未遂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于犯罪中止,故对犯罪未遂的处罚应当重于犯罪中止。这一解释通俗易懂,所以接受者甚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客观主义无法解释为何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重于犯罪中止。
在犯罪过程中,无论行为人多么努力地防止既遂结果的发生,只要既遂结果发生了,如故意杀人后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但被害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的,这时属于既遂犯,不构成中止犯。由此可见,犯罪中止之所以能够受到宽大对待,主要不是因为其人身危险性降低了,而是其在客观上消灭了犯罪既遂的危险,使得法益免受毁灭性侵犯。
在未发生既遂结果这一点上,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相同,但在未能发生既遂结果的原因上,二者存在重大不同:犯罪未遂并非行为人本人消灭了既遂危险,而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障碍导致既遂结果无法发生;与此不同,犯罪中止则是行为人自动消灭了既遂危险,因而既遂结果无法发生。在犯罪的过程中,容易控制犯罪过程的人当然是行为人本人,从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法益出发,刑法号召行为人若能自动消灭既遂危险,即可得到宽大处理;而犯罪未遂的行为人未响应刑法的号召,刑事责任自然应重于犯罪中止。由此可见,完全可以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解释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重于犯罪中止的原因。
综上,将犯罪未遂理解为已经爆发但由于其他原因未能造成应有损害的风暴,是既形象又合适的,借此可以很好地理解犯罪未遂的法律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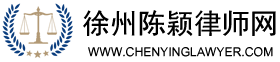
 所在位置:
所在位置:



